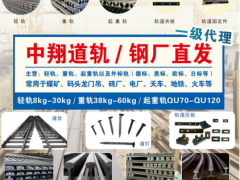電氣化日益滲入各行各業的今日,仍有部分職業很難擺脫對化石動力的依靠,這些職業被稱為去碳化“老大難”,如航空、長途運輸、煉鋼和水泥制作,以及牢靠的電力供給等。氫氣被視為完成這些職業去碳化的最佳選項,而以氫為根底制作碳氫化合物并完成去碳化的燃料被稱為氫燃料,近期更是受到必定程度的追捧。
近期有關大眾方針的討論尤其關注這一領域,特別是在歐洲,一些方針決議計劃人和研究人員也都大力呼吁,在更大范圍內用氫燃料代替天然氣。波茲坦氣候應對研究院新近出爐的陳述分析了氫燃料作為代替動力的利害,以為其確實能有效挖潛低碳且廉價的太陽能和風能發電,最終又能運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得到氣態或液態的燃料,具有能量密度高、可儲運和可焚燒等特色,然后成為代替化石燃料的完美選項。
氫燃料是二次動力載體,運用過程中有轉化丟失
但實際上,氫燃料之所以被看好,最大原因是其能夠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建立一個橋梁,允許內燃機和其他以焚燒化石燃料為主的設施繼續存在,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大環境下找到新的定位。人口密度大、缺少太陽能和風能的區域,也可通過全球商場進口氫燃料。
但波茲坦氣候應對研究院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氫燃料的弊端也很明顯,它是二次動力載體,在供給端和終端用戶的運用過程中都存在額定的轉化丟失。根據應用場景和相應的技能,氫燃料將電轉化為可用動力的功率在16%~48%。換言之,假如按發電量核算,氫燃料所需的電量是直接用電代替物所需電量的2~10倍。這其間的丟失超越可再生動力豐富的國家用電和將其以氫燃料出口獲得的收益。
從供給端來看,氫燃料的出產至少需求兩個轉化步驟:電解和烴的組成,從電到燃料的功率丟失為50%,其間包含從空氣中捕集二氧化碳時所需的5%左右的電量,而這個過程中所需的熱量也將耗去總電力的20%,但考慮到能夠運用其他途徑的廢熱,故在核算中將之忽略。
從需求端來看,焚燒氫燃料做機械功時,轉化能效低于20%,也即焚燒氫燃料的內燃機汽車所需的電量是電動汽車(可再生動力電力)的5倍,且后者的轉化環節更少,也不依靠內燃機,有效能運用率更高。
2030年前,氫燃料還不具有競爭性
在對比分析了氫燃料、化石燃料和直接電氣化的經濟性后,該陳述以為,氫燃料短期內不或許完成低成本充沛供給,然后大范圍代替化石動力,其推行首要依靠方針扶持。現在還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推行支持行為,至少在2030年前,碳稅的水平還不足以使氫燃料具有競爭性。因此氫燃料的前景現在還不明確。
考慮到當時氫燃料的稀缺性,進行氣候和動力方針決議計劃時應在價值排序的根底上,確認在哪個領域開發氫燃料的終端用戶。引導特定氫燃料終端用戶的規章和方針應系統性地考慮在其他場合運用氫燃料的機會成本。在當時急需進行碳中和與減排的布景下,有限的氫燃料應優先考慮用于無法或難以通過直接電氣化和其他挑選完成這一目標的職業,但這并不必定是指那些氫燃料最具競爭性或去碳化老大難職業。
氫燃料不應成為大范圍直接電氣化的阻礙,假如押寶于氫燃料的大開展而忽視終端運用轉型,一旦氫燃料的規劃達不到預期,或許陷入對化石動力的徹底依靠。
氫燃料不太或許促進2030年氣候目標的完成,原因是其功率首要取決于是否有較高的電轉化率,與之相比,低碳電力通過直接電氣化能夠更有效地削減碳排放。
中期來看,氫燃料的競爭性取決于碳稅的高低。長時間來看,氫燃料一方面有助于解決人口密度高、可再生動力匱乏區域的減排問題,如德國、日本、韓國等;另一方面可為可再生動力豐富的區域,如西亞北非、冰島、拉美和澳大利亞,創造動力出口機會。從這個角度看,氫燃料可將太陽能“打包”在全球進行交易,縮小可再生動力供給與動力需求之間的距離。但要建立這樣的商場,在方針層面將是極大的考驗。
開展氫燃料應將其置于全體轉型戰略中,其間包含根底設施的設計,而電力、二氧化碳、氫氣直接運用的程度將決定根底設施的設計。中國石化報 作者:盧雪梅
近期有關大眾方針的討論尤其關注這一領域,特別是在歐洲,一些方針決議計劃人和研究人員也都大力呼吁,在更大范圍內用氫燃料代替天然氣。波茲坦氣候應對研究院新近出爐的陳述分析了氫燃料作為代替動力的利害,以為其確實能有效挖潛低碳且廉價的太陽能和風能發電,最終又能運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得到氣態或液態的燃料,具有能量密度高、可儲運和可焚燒等特色,然后成為代替化石燃料的完美選項。
氫燃料是二次動力載體,運用過程中有轉化丟失
但實際上,氫燃料之所以被看好,最大原因是其能夠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建立一個橋梁,允許內燃機和其他以焚燒化石燃料為主的設施繼續存在,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大環境下找到新的定位。人口密度大、缺少太陽能和風能的區域,也可通過全球商場進口氫燃料。
但波茲坦氣候應對研究院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氫燃料的弊端也很明顯,它是二次動力載體,在供給端和終端用戶的運用過程中都存在額定的轉化丟失。根據應用場景和相應的技能,氫燃料將電轉化為可用動力的功率在16%~48%。換言之,假如按發電量核算,氫燃料所需的電量是直接用電代替物所需電量的2~10倍。這其間的丟失超越可再生動力豐富的國家用電和將其以氫燃料出口獲得的收益。
從供給端來看,氫燃料的出產至少需求兩個轉化步驟:電解和烴的組成,從電到燃料的功率丟失為50%,其間包含從空氣中捕集二氧化碳時所需的5%左右的電量,而這個過程中所需的熱量也將耗去總電力的20%,但考慮到能夠運用其他途徑的廢熱,故在核算中將之忽略。
從需求端來看,焚燒氫燃料做機械功時,轉化能效低于20%,也即焚燒氫燃料的內燃機汽車所需的電量是電動汽車(可再生動力電力)的5倍,且后者的轉化環節更少,也不依靠內燃機,有效能運用率更高。
2030年前,氫燃料還不具有競爭性
在對比分析了氫燃料、化石燃料和直接電氣化的經濟性后,該陳述以為,氫燃料短期內不或許完成低成本充沛供給,然后大范圍代替化石動力,其推行首要依靠方針扶持。現在還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推行支持行為,至少在2030年前,碳稅的水平還不足以使氫燃料具有競爭性。因此氫燃料的前景現在還不明確。
考慮到當時氫燃料的稀缺性,進行氣候和動力方針決議計劃時應在價值排序的根底上,確認在哪個領域開發氫燃料的終端用戶。引導特定氫燃料終端用戶的規章和方針應系統性地考慮在其他場合運用氫燃料的機會成本。在當時急需進行碳中和與減排的布景下,有限的氫燃料應優先考慮用于無法或難以通過直接電氣化和其他挑選完成這一目標的職業,但這并不必定是指那些氫燃料最具競爭性或去碳化老大難職業。
氫燃料不應成為大范圍直接電氣化的阻礙,假如押寶于氫燃料的大開展而忽視終端運用轉型,一旦氫燃料的規劃達不到預期,或許陷入對化石動力的徹底依靠。
氫燃料不太或許促進2030年氣候目標的完成,原因是其功率首要取決于是否有較高的電轉化率,與之相比,低碳電力通過直接電氣化能夠更有效地削減碳排放。
中期來看,氫燃料的競爭性取決于碳稅的高低。長時間來看,氫燃料一方面有助于解決人口密度高、可再生動力匱乏區域的減排問題,如德國、日本、韓國等;另一方面可為可再生動力豐富的區域,如西亞北非、冰島、拉美和澳大利亞,創造動力出口機會。從這個角度看,氫燃料可將太陽能“打包”在全球進行交易,縮小可再生動力供給與動力需求之間的距離。但要建立這樣的商場,在方針層面將是極大的考驗。
開展氫燃料應將其置于全體轉型戰略中,其間包含根底設施的設計,而電力、二氧化碳、氫氣直接運用的程度將決定根底設施的設計。中國石化報 作者:盧雪梅
 手機版|
手機版|

 關注公眾號|
關注公眾號|


 下載手機APP
下載手機APP